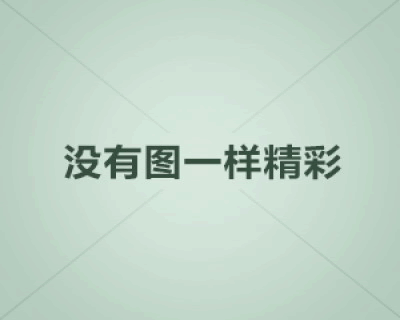碧海银沙网讯(文/宋立民编辑/金 臻 蔚 青)【按】日前读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》,至“由于居住条件困难,有一段时间,闻一多教授、华罗庚教授不得不两家共住一间大屋,中间用布帘相隔”。是的,“布东考古布西算,专业不同心同仇”——忽然记起7月15日是闻一多先生逝世70周年。无论是爱国情怀,还是治学精神,先生都是旷世的楷模。今根据历年来读书笔记,写几句先生的教书,一是“为了忘却的纪念”,二是也算“虽不能至心向往之”。
1、上学期讲完鲁迅专题,与几位同学讨论“满堂灌”的问题,我说可以留一点时间互动,但是我的课基本上是“灌”,有问题下来说。恩师宋景昌先生是闻一多的学生,说西南联大那时节名师们多半也是灌,课堂讨论的不多。问题在于灌的是啥东西。如果是活东西,是学问,学生学而不厌,照样不会觉得“死”。灌死知识,字字抄笔记,大家当然不喜欢,即便不灌而改为提问之类,照样没有用,浪费生命。
2、以往看到过不少西南联大的回忆录,提及闻一多先生的授课。如汪曾祺先生就回忆过:闻一多先生上第一节课,打开高一尺半的很大的毛边纸笔记本,抽上一口烟,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:“痛饮酒,熟读《离骚》——乃可以为名士。”闻一多先生讲唐诗,把晚唐时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,为其他大学所无。他的课非常叫座,连工学院的学生都穿过整个昆明城赶去听,大教室里外都是人。
而且,更醉人的是,闻先生的课从不考试,期终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。
3、精兵精讲。1933年下半年,清华。只有孙作云与王文婉两人选了闻一多的《楚辞》课,先生照样“拼命地预备功课,全心全意地为我们讲解。因为教室人少,讲书如同座谈,所以我们几乎每一句解释必问出处,闻先生总是聚精会神地给我们讲。”
4、没有“学术秘密”。当时没用课件与电子文本、博客等,老师的讲义实在是今天的“科研秘密”,而且人家确实是有货的讲义。但是“闻先生向来就未把学问当做自己的私产,他把自己的心得告诉学生,把未发表的笔记或讲义借给学生抄,那是司空见惯的事”。
5、教书以一当十。闻一多先生讲课重点十分突出。从不按部就班、一二三四、蜻蜓点水、面面俱到。“半年的功夫读完了一篇《天问》。同时,也就这样,奠定了我一生做学问的基础”。正如陈寅恪在《柳如是传》里写出了历史、学问与自己一样,一篇《天问》同样可以讲尽屈赋、楚辞、诗情、风骚。讲什么已经不那么重要,重要的是谁来讲、如何讲。好像钱理群讲现代文学史只讲周氏弟兄,此之谓也。浩浩唐代文学,我们能够讲几个作家?30年现代文学,十八罗汉足矣。
6、对学生的鼓励。“闻先生对我总是有些偏袒之见罢,平日向闻先生请教时,凡我之所言,闻先生几乎无不是之;其实,有的地方,到后来连我自己也改嘴了,但在当时,闻先生总是千方百计地鼓励我,他认为我是一个可以继承他的衣钵的人,我不妨这样夸诞地说。”据说大师多是通过鼓励暗示出来的。这一点我做的不够,我一般不批评学生,但鼓励也不多。
7、讲成散文。1928年3月《新月》杂志创刊。而闻一多的教学、研究与创作同样是合一的,可见这样的同步也并不新鲜。例如他上课讲老杜,就把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心得写成《杜甫》一文发在杂志上。说是尝试,但是“它不是论文,而是试图给伟大诗人杜甫画像的传记散文”,而他的研究归结为写杜甫的传记,这样文字最适合做讲义。
8、知识深广程度。研究如何从平凡进入不平凡?闻一多作出了表率。由于研究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的需要,闻一多开始了古文字甲骨文、钟鼎文的研究——这在今天的教授几乎不可能。我们的文学老师对于语言常常捉襟见肘,而教汉语的老师甚至不会写一篇哪怕小小的散文,上课的时候除了讲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讲义一无所有,也无挂怪乎学生怨声载道。而闻一多是“学术研究总是自辟道路,直探本源,不甘因循守旧,依靠传统注疏以解决通读古籍的文字问题。这当然是钻故纸堆,愈钻愈深愈广,需要精神,也需要见解、能力和气魄。”在时下之浮躁的大海里,闻一多怕是后继无人了!
9、美丑一并指出。孙作云有了学术见解,闻一多及时鼓励。然而,当孙的“处女作”论文《九歌山鬼考》交给闻一多之后,“他看了一看,一面点头,一面又叹气,说:‘这个意见很好,那个意见也不错,只是文章啊!——’”以先生的学术功底看学生的文字,自然千疮百孔。但是,接下来是自己与助手动手改,直到发表。如今有水平的教授一般没有功夫好好改学生的“幼齿”之作,没有水平的自己还写不出,更不用说指导学生。真的想培养一个像样的弟子,不容易呀。
10、上穷碧落下黄泉。1938年5月4日,西南联大开始上课,文法学院设于蒙自(十年前笔者到弥勒,有心去蒙自看看,终付阙如),几乎世外桃源,闻一多写作备课,在教工宿舍楼居高不下,同事戏称为“何妨一下楼主人”。这才有“讲《天问》手里拿着四易其稿的《天问疏证》,一句一句地讲,一个子也不含糊,详征博引,一学期只讲了一篇《天问》”。
当初笔者读大二,几位老先生讲古文学,说:“你看这注释,你明白的他使劲注,你不懂的他一句不讲!”无它,功夫不到,又不敢像文怀沙先生注鲁迅诗信口开河也。
11、“史”与“哲”的发掘与用处。1939年暑假之后,闻一多先生居然有一年的“科研假期”(我们现在基本上望假兴叹了),他蛰居晋宁小城,整理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《乐府》、古代神话等旧稿外,又进一步研究《易经》,“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《周易》,不主象数,不涉义理,计可补苴旧注者百数十事。”后人把周易的哲学折腾成算命的“玄学”,然而闻一多先生则从文字训诂入手,发掘古代社会史料。这一切与他后来在联大的讲授《诗经》、《中国古代史分期研究(一)》、《先秦两汉文学史》、《古代神话》等课程无疑有着深入与拓宽的作用。如今大学教师备课的一大难点是就事论事,无法左右逢源,盖“史”与“哲”基础太差之故。我们读中文系有系统的中国通史课开,现在连中学都因为高考而不再学历史了,可悲乎哉。而“可补苴旧注者百数十事”,亦可见用功的深广。
12、关于训诂学。不少回忆提及:闻一多精力充沛,研究兴趣广博。其案头常备高邮王氏父子的《读书杂志》、《经义述闻》等,认为乃文字训诂之学的“经典著作”。盖清代以前,中国传统语言学一分为三:1)《说文》为宗的“字学”;2)《尔雅》为宗的雅学;3)《切韵》为宗的音学。三线平行,少有人从相交与依存的角度思考。“自从顾炎武开辟榛芜,戴东原确立大法,段玉裁、王念孙继以专著”,传统语言学这才进入综合运用阶段。而闻一多正是从“综合”与“融汇”的意义上找到通读先秦古籍的方法。其在《楚辞校补•引言》中指出:“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,大概不出三种原因。(一)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,因年代久远,史料不足,难于了解;(二)作品所作的语言文字,尤其那些‘约定俗成’的白字(训诂家所谓‘假借字’),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;(三)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讹误,往往也误人不浅。《楚辞》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,所以在研究它时,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,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:(一)说明背景,(二)诠释词义,(三)校正文字。”又说:“三项课题本是互相关联的,尤其(一)与(二),(二)与(三)之间,常常没有明确的界限,所以要交卷最好是是哪项课题同时交出。”朴学+文史(包括民俗、心理、宗教、思想),使得闻一多迅速站到了高邮王氏的肩头。——如今将文学的教授又有几位把训诂引进自己的讲义的呢?
笔者廿年前做《中华别称类编》,发现自己对于训诂的忽略与无知带来了不少麻烦,于是一边干一边补训诂的课,前前后后好几年,完全与现代文学、鲁迅与新闻无关。偏偏后来那书盗版最多,实用价值最大。以至于几位博士师弟直截了当:老兄,你弄鲁迅是几万人里挑一,轮不到你领头,而摆治这个“称谓文化”,全国没有几个人,你是绝对权威。其实,在钱钟书、郑逸梅等先生的论著里,笔者早已看到专门对于别称的论述,吾等也是刚刚入门而已。
13、关于教书与政治。闻一多先生早年在清华是极其讨厌“清华的美国化”的,到了美国以《红烛》表达思念祖国的情绪与对于压迫的厌恶,政治色彩很浓。而后来做了学者,又接受“国家主义”思潮,一心踏踏实实做学问,不大过问政治。但1943年后,选新诗、评田间、思想跃进,故态复萌。更重要的是经历此“否定之否定”而义无悔改。他说:“我的文章才渐渐上题”。于是,不安分的学生、情如火的诗人、宏博的学者——终于重回带火的斗士。
文如其人,课如其人。力图脱离政治而一心钻故纸堆者,怕是也钻不深透的。
14、小结。郭沫若先生说“‘千古文章未尽才’闻一多先生的大才未尽,实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。”“一多对于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,内容很广泛,但他所致力的对象是秦以前和唐代的诗和诗人。关于秦以前的东西除掉一部分的神话传说的再建之外,他对于《周易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庄子》、《楚辞》这四种古籍,实实在在下了惊人的很大的工夫。就他所已完成的而言,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着,他眼光的犀利,考察的赅博,立说的新颖而翔实,不仅是前无古人,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。这些都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信口开河,凡是细心阅读他这《全集》的人,我相信都会发生同感。他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,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,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。他是为了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,为了要扬弃古代而钻进古代里去刳它的肠肚的。他有目的地钻了进去,没有忘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,这是那些古籍中的鱼们所根本不能想望的事。”——闻先生的著作就是他的讲稿,更是他的人格。做学问与做人、与教书高度的一致,或许也是研究的正途、后学的楷模。